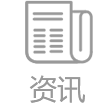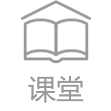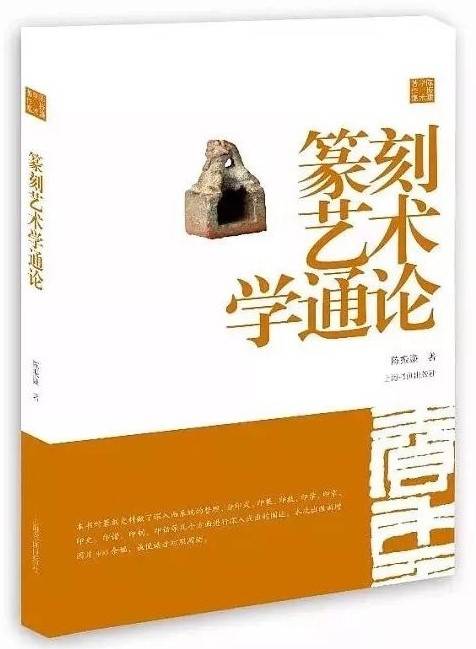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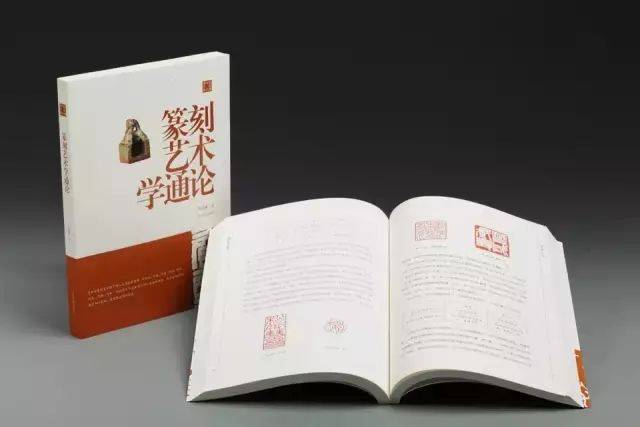
《篆刻艺术学通论》再版前言
■陈振濂
以前没有想到过我的工作会与西泠印社和古典印学、金石学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少时遍读各家书,忽然发现有一个奇怪现象: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沙孟海,民国艺术界的这些巨子们,不约而同,都有一部《印学概论》传世。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都是以画称雄一世,怎么都毫无征兆地一式对印学如此热心?
刻印向被指为雕虫小技,但印学却又惹出这么多大师巨匠的青睐,其中的关系可是非同简单。早年在上海,刻印读印是青葱时代最深刻的回忆。记得那时在狭窄的小房间里描摹古印四大册三千多方,还曾经为高式熊前辈夸赞有加,说我这样的笨功夫花得值,将来会受益终身。到了中国美院,刻印以外,陆维钊师命我点古书,第一部就是清代朱象贤《印典》,边点句边对照时贤如邓散木的《篆刻学》和当时好不容易托表姐从香港携来的钱君匋叶露渊著的《中国玺印源流》,终于有了一个对古玺印在知识上的认识框架。随着我自己不断刻印、读印,又因为西泠印社八十周年社庆1983时受上海《书法研究》约稿写一长文《印学话西泠》,以及后来考证西泠印社创始人、考证吴隐、考证古代印谱的起源、又涉足篆刻美学并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专论……一时间篆刻艺术研究几乎成了我的学术生涯中的最大主题。于是,就有了写一部篆刻专书的愿望。1983年底完稿,最初定名为“印坛漫步——篆刻艺术的历史观与美学观”,后来出版社方面的意见是“书名太像论文集,不好卖”,希望改为“纵横谈”以求符合大众口味,那时我人微言轻,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是物资匮乏,出版一本书大不易,故尔不再持异议。今天想来,“纵横谈”容易被误解为茶余酒后的随笔短札,即兴而至,片楮零简,不成体系;顺手看看无妨,不看也无大所谓。但关于这部书,却有完整的构架,从[印式]开始,[印篆]、[印技]、[印学]、[印家]、[印史]、[印谱]、[印制]、[印语]共九章,是事先设定了一个明显的学术结构。它是有序的、比例均匀的。因此,“纵横谈”应该不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书名。入门级的篆刻爱好者,或有一定积累的专家,都可以从这部书中找到所需要的内容,遂新定名为《篆刻艺术学通论》。它首先是“论”,相对比较严肃而不是随口海侃不着边际,但它又“通”,涉及方方面面,而不是论文集那样的专题性太强又太窄。
但更重要的,是我特别选择了一个不平常的论述角度。作为“印学”(历史学、考古学、金石学)的立场,和作为篆刻艺术的审美立场,应该是不同的。过去的类似著述,要么以技巧即刀法篆法运用居先,要么以印学史居先;前者是技艺,是直觉;后者是史述,是凌空,但都不是审美居先——而篆刻艺术是“艺术”,本来应该审美居先。而审美居先,必定是以可视的形式为主导。故尔我们这部“通论”第一章,即先列[印式]即印章或篆刻形式研究。它的内容分布,有印材、印文(篆书)、花押、楷隶书印、图像印,以及朱白文,边框、外形、尺寸等等各种形式审美要素的排比与分析。而第二、三、四、五各章,分别是篆(文字),技、学(典籍)、人(印家),它们都是为了篆刻审美形式而存在的。而在学术上更有独特性的,是[印谱]、[印制]两章。近代谈印学,基本不涉及“印谱”现象,但它恰恰是印学(篆刻)生存绵延的最根本的社会传播载体和物质载体。针对这种因为观念局限所带来的重大遗漏,本书予以充分的补充和展开。又[印制]即古代官制与官印的关系,过去也是攻历史与考古的学者感兴趣的内容,篆刻艺术于此是大多视而不见的。但我们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章节来对待,予它以一种“印文化”与应用环境的重要意义而为印学研究所不可怠忽。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架构,这两者都是前人未注意而我们重新赋予其价值的。
作为常态的近代篆刻著述,即使是知识介绍,有系统的已极少;而要有学科框架意识的更少。十几年前,学术界兴起“方法论”的大讨论;但在篆刻理论界,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方法论问题。平铺直叙的知识铺排,专题研究中多借鉴考据、史述的现成方法,这样的著述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一是篆刻的小众使它难以有大平台驰骋空间,人才储备严重不足。二是篆刻理论多坠于工匠的经验叙述而缺少学理意识。而在此中,建立学科意识和框架可能是最当务之急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篆刻艺术学通论》这样的书仍然具有它特定的存在价值。
三十年来,在篆刻艺术研究方面,我在下述几个专题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自谓是在学术上尽量体现出“发前人(时人)之未发”的愿望和初衷。
1.篆刻美学
从1986年开始,受命作篆刻艺术美学研究的专论。当时正值全国知识界“美学热”,诗词美学、小说美学、书法美学、中国画美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我自己就是当年书法美学论战中的主角之一,又写过三部不同的《书法美学》著作。《文艺研究》编辑部认为传统艺术范围内的美学研究,只有一个篆刻还是盲点。但市面上所谈的篆刻美学,大都是谈篆刻美的欣赏,较为泛泛而缺乏美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与逻辑框架,谈不上“美学”。因此命题要我做一篇真正的、专业美学家读了也不得不赞成的篆刻美学论文——不要面面俱到的知识介绍,要有清晰准确的思辩力和穿透力。于是以一周之功完成《篆刻美学导论》二万言,刊发在《文艺研究》1987年第2期上。同时,又在篆刻的创新与继承这些最热门的话题中,相继发表了《篆刻古今盛衰论》(《篆刻家》1985年第1期)《独立:篆刻本位的观念确立(上)(下)》(《中国篆刻》1994年8月创刊号第1、2期)等。我以为,尤其是当时这篇《篆刻美学导论》长文的作用,是为“篆刻美学”这一学科划定了一个框架,确定了一种学术规范,只可惜后来应者甚稀,受到篆刻界人才知识结构的影响局限,未能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响应而已。
2.古印谱考证与印谱史研究
从80年代初热衷于考证印谱起源,撰《关于印谱的创始者》1981,《啸堂集古录考》1985之后,在90年代末有一个契机,编辑了《中国印谱史图典》上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这部大书,还撰写了《中国印谱史研究》的五万言长文。这样,印谱起源和创始、印谱史研究,就成了我一直为之用功的一个学术领地。也即是说,从1981年到1999年再到2011年,横贯三十年间的持久努力,构成了于我个人而言非常清晰的学术刻痕。在今后,随着在这方面的积累越来越丰厚,这样的投入还会更加经久不衰。
3.篆刻高等教育教程
在进行高等书法教育研究的同时,必然会考虑同样的努力应当投入大学专业级的本科篆刻教育教学研究。但在此中困难点是在于,篆刻学习的技能性特别强,比如我们很难证明或界定出:哪些是专业级(而不是业余级)的、哪些是艺术教学(而不是技能型教学),但正是依靠篆刻美学研究所获得的学科思维优势,又有书法高等教育的科研探索在前,在2000年,完成了一部《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篆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并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其实直到十几年以后,何为篆刻的高等教育?它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区别和边界如何划分?在我们的篆刻领域里都是含混不清的。因此,《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篆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一书第一次提出并清晰勾画出高等篆刻艺术教育的学科内核与外延诸内容,这在篆刻史、篆刻教育史上都是第一次。
4.域外印章研究的倡导
以2016年为界,过去我们对篆刻创新的提倡,是有一个固定的思路:这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当然,十余年来以西泠印社为平台,关于肖形印、关于现代肖像印,我们的新提倡还是突破了一些惯性思维,取得了一些丰硕成果。但借助于G20杭州峰会召开的千载难逢机遇和“城市国际化”的发展目标,我们组织倡导了“图形印与非汉字系列印章国际学术讨论会”,彰显出一种全新的篆刻发展理念。目前才刚刚开始启动,有了第一阶段的成果,后面还会有一系列关于创作和关于理论研究的策划。
2017年年初在全国“两会”期间,为沙孟海先生的《印学史》作导读文字,特别谈到了沙老在一部极简要的《印学史》中竟然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地内含了四大创新点并且拥有各自明显不同的方法论特征。不经发掘,或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积累,或许还真体会不出一代大师学宗的卓绝之处。那么我也有一个心愿,我们做学问写著作,应该也要向这样的典范学习,即使在一个平凡无奇的题材中,也能提炼出精彩纷呈的含量和主题,追求卓越,反对平庸,如果在多年以前的这部《篆刻艺术学通论》中,还能够发现它在今天仍然有一些不甘于平庸即不取传统式的简单移植抄录的时弊的优点的话,那就不枉了再次重版之诸君付出的辛勤劬劳了。
2017年6月10日于南京——杭州高铁途中
文章来源: 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