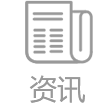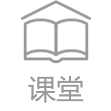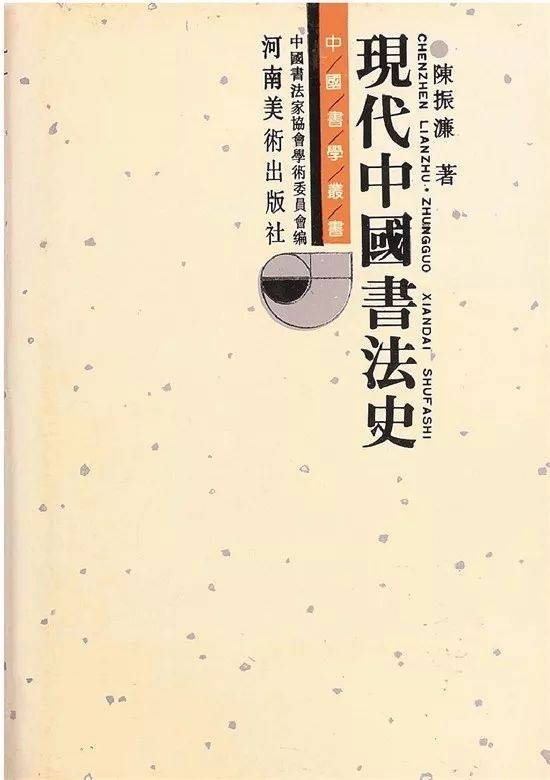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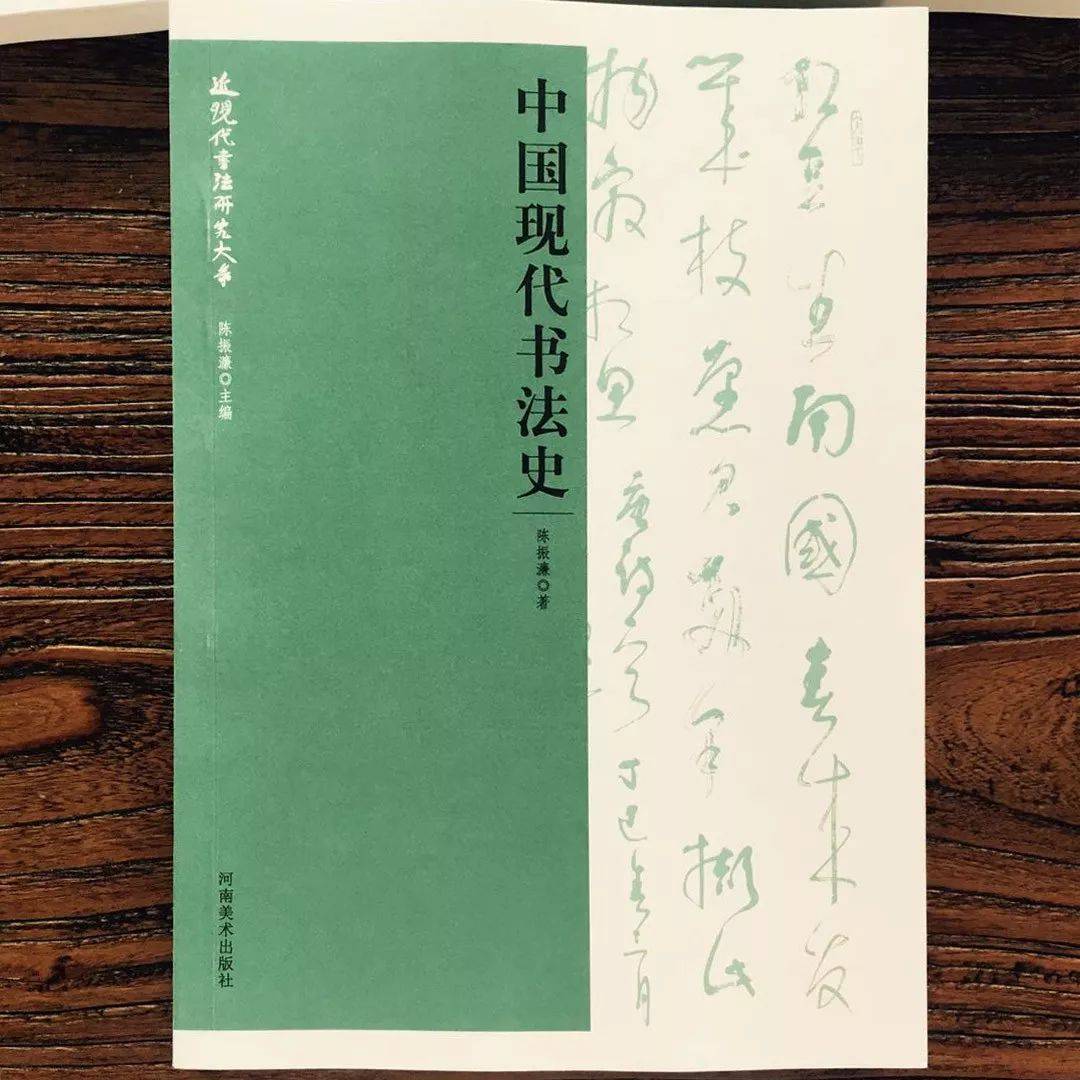
近现代梳理的“历史定位”与方法论上的
“史观学派”——《现代中国书法史》再版前言
■陈振濂
1979年我在读浙江美院研究生时,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先生对我的研究方向的讨论,指定是宋代书法史。两年之间,我熟读了大批宋代文化史籍,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功课作业。有了相应的“本钱”,其后陆续开始致力于宋词流派美学研究,宋代花鸟画折枝构图研究,宋代钱币研究,宋代文人篆刻研究,宋代印谱研究,宋代款书款印使用研究,宋代文人画研究,都是从宋代书法研究中延伸出来的系列成果。
与宋代书法研究的纯学术立场相比,近现代研究的发端却可能是基于一个不无实用的出发点。第一是当时应邀为刊物杂志写了不少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陆抑非、沙孟海、陆维钊、以及西泠印社史的文章,涉及了相当多的近现代书画篆刻的史料;第二是当时十几年间对日本书法与中日交流史的投入很大,而这个领域中同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近现代书法绘画篆刻史资料的支撑,甚至在对日本近现代书法史研究的过程中,会不断涉及杨守敬、黎庶昌、张裕钊、吴大澂、王冶梅、吴昌硕、王一亭、廉南湖、吴芝瑛、郭沫若、钱瘦铁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要了解当时中国与日本的交流的事实和意义,细致调查并把握这些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的经历、交游、思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慢慢地,觉得在近现代书画篆刻方面,想了解的事实、想发表的见解,越来越多,不吐不快。于是,“宋代书法史研究”之外,又有了一个“近现代书法(民国书法)研究”的新开拓。
近现代书法史的系统研究,在上世纪80-90年代几乎是空白。1987年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在贵州召开第二次会议,提出要组织撰写一套[学术丛书],原来提出要我写宋四家的“尚意书风”,但我的直觉,是写宋代不过是在众多成果中的多一项;而如果选择“民国书法史”或“近现代书法史”来做一次高端又系统的研究,则可能是一项破天荒的开创性工作。我当时还年轻,血气方刚,有很强的事业心,当然是选择近现代。费时不到一年,《现代中国书法史》于1988年成稿,但[学术丛书]却迟迟未能落实到位,直到1993年,才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虽然被搁置了五年,但终于了却了一个毕生的学术理想。
出版后在中国的反响还说不出什么,但在日本却引起关注,西岛慎一先生是日本二玄社(专门从事书画出版的最大出版社)董事总编辑,书法界的元老前辈,今年已近九十了。他亲自策划经历了台北故宫古书画复制的大工程,与启功、饶宗颐、谢稚柳等皆为莫逆之交;又是日本大家西川宁、青山杉雨的挚友。他经手经眼的古书画和近现代书画不计其数,他有一次在东京的聚会中对我说:“刚刚读到陈老师写的《现代中国书法史》,极其有趣,梳理清晰得当,纷繁的近现代书法,一大批人物首次都有了恰当的历史定位,很珍贵的史料啊!”
研究近现代史,史料问题当然重要,但我更在意的是“第一次作出历史定位”的评价。因为这正是一个史学家的主要职责与使命。它需要史德、史学、史识的综合优势条件。而“近现代”因为刚刚发生,所以还是会纷繁芜杂,鱼目混珠,良琇不齐,在一个无良史家面前,会出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因此,准确的适合的历史定位,和清晰的梳理,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最重要责任。所以,我把西岛慎一前辈的评价,看作是对本书的最高褒奖。
谈到具体的“历史定位”,本书对清末、民囯直到1949年后乃至上世纪80年代的各阶段各时期书法界的代表性人物、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认真的筛选和排列,提取出至为重要的历史节点。提出了在百年之间第一层级的书法大家、第二、三层级的书法名家,以及各个书法社团组织、书法报刊、书法家的社会姿态与专业角色,尤其是在1988年这方面学术成果积累还乏善可陈之时,首次提示了:1清末甲骨文西北汉简西域残纸三大考古发现;2民国时期第一次书法展览会举办;3“标准草书学社”与《草书月刊》;4重庆中国书学会和《书学》刊物编辑;5西泠印社;6五十到六十年代日本书法代表团访问中国和中日互办书法展览;7毛泽东主席赠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怀素自叙帖》;8《人民中国》(日文版)书法专刊;9“文革”后上海《书法》杂志创刊;10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11“书法美学大讨论”等等的重大书法史实。与习惯上的旧有模式热衷于斤斤计较书法家中孰为大师孰为凡庸的地位相比,这些超越于个人作为和成就高下的历史事件、现象还有影响的存在意义要重要得多;作为“近现代书法史”的历史发展节点把握,也要关键得多。它可以告诉我们:过去我们虽然有二十四史的史学传统,但遗憾的是,民国以来新学兴起,落脚到书法研究上,却把一部浩瀚五千年的历史,简化成一部人物(书法家)的《帝王本记》、《将相列传》式的组合拼接史;而丝毫没有对历史事件、现象的把握和梳理提示。于是,本来是生机勃勃、生动活泼的千变万化的书法史,却成了干巴巴的“点鬼簿”、“名人录”。味同嚼蜡,令人昏昏欲睡。
正是基于这一史学反思,在8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红极一时的书法“史料(考据)学派”引经据典辨伪证史、还堂而皇之地引用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之说法以自诩正统的大背景下,我们坚决提出,“史学是思想之学”,并集合同道,倡起了一个轮廓分明的“史观学派”。它的思想逻辑起点有两个来自外部大历史研究学界的来源:一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二是顾颉刚的“累层地建造起来的中国古史”。而作为在书法界“史观学派”的倡导者,我自己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如关于印刷术与中国书法出体演变的关系、又如关于“展厅文化”对当代书法史进行全面塑形的分析研究等等,除此之外,还写了两部意在呈现“史观学派”基本形态的著作:一部是《线条的世界——中国书法文化史》,后由浙江大学出版;另一部就是这本《现代中国书法史》,在时间上先面世。当然,如果算上书法史教材的话,那范围也许更大。
记得在讨论“史料(考据)学派”和“史观学派”之间关系时,大家本来都有一个共识:没有占有史料,言而无据,当然谈不上历史研究。但如果把书法史研究写成《书法人名大辞典》式的条目的拼合,那当然不是历史研究而只是一个资料汇集。本来,这应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但如果史料考据一家独大盛气凌人,真以为“史学就是史料学”;那么物极必反,倡导“史观学派”,就要在观念和方法上多做文章。我在那时候的很多场合,都提出过一个判断的标志:在撰写书法史时,有没有本领把传记文献资料和“引文”都转成[注],除非极个别的需要,坚决不在正文中出现。看看在把引用资料都转列于[注]之后,你的正文还能写些什么?许多著作貌似学问深厚,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但一旦把引文都转成[注],正文几乎溃不成军,完全不成文句意思。我想,只有把引文资料和文献都转成[注]后你的文字仍然通畅犀利、条理清晰、意思饱满,那才是写作高手。“史观学派”要的正是这样的治史境界。是我要说什么,而不是古人说了什么我再介绍或附和赞同什么。
这样立足于两端的思考与争辩,在二十年前可谓是十分新锐的。但它造就了我们这个书法史研究时代的跌宕起伏,波诡云谲;在为我们在学术上找到很多对立面同时,也让我们时时不忘检验和反省自己,生怕一有疏虞授人以柄,至使整个“史观学派”的确立受到不良影响。所幸的是,随着学术日益进步,尤其是高校博士生教学对于学位论文指导过程中“问题”意识的义无反顾的强调,书法史研究中的“史观”的支配作用越来越为学子们所认可和尊重。鉴于此,“史观学派”作为一个超越常识介绍事实罗列的更高端的学术形态;包括它所主张的“史观”主导也越来越有足够的底气,受到学术研究的追捧,从而显示出它的无所不在和无远弗届。
书法史学研究方法是一门大课题。在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的博士生课程中,有一门“中国美术史学史”,专门针对这个史学研究方法而来。“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在大历史学科中都有极好的范本可举。本来两者皆不可偏废。但在特定的时期,以放眼一个时代的宏观视野,适当强调某一学派以倡导新锐或求取平衡,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平衡和协调,本来也就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以此来看这部《现代中国书法史》,在点出它本身的“历史定位”的学术价值之外,再提示出它在90年代前后作为“史观学派”尝试而试图协调“史料(考据)学派”的一面倒的正统意识以求学术生态的健康生长,今天回过头来想想还是很有必要的。
当下中国书法史研究中的“史观学”的新硎初试之作;又是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尝试为近现代书法史中纷繁杂乱的人与事作“历史定位”的率先之作。这是今天再版此书的意义所在。
希望读者诸公能喜欢它。
2017年8月23日于浙江桐乡
文章来源: 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