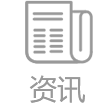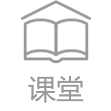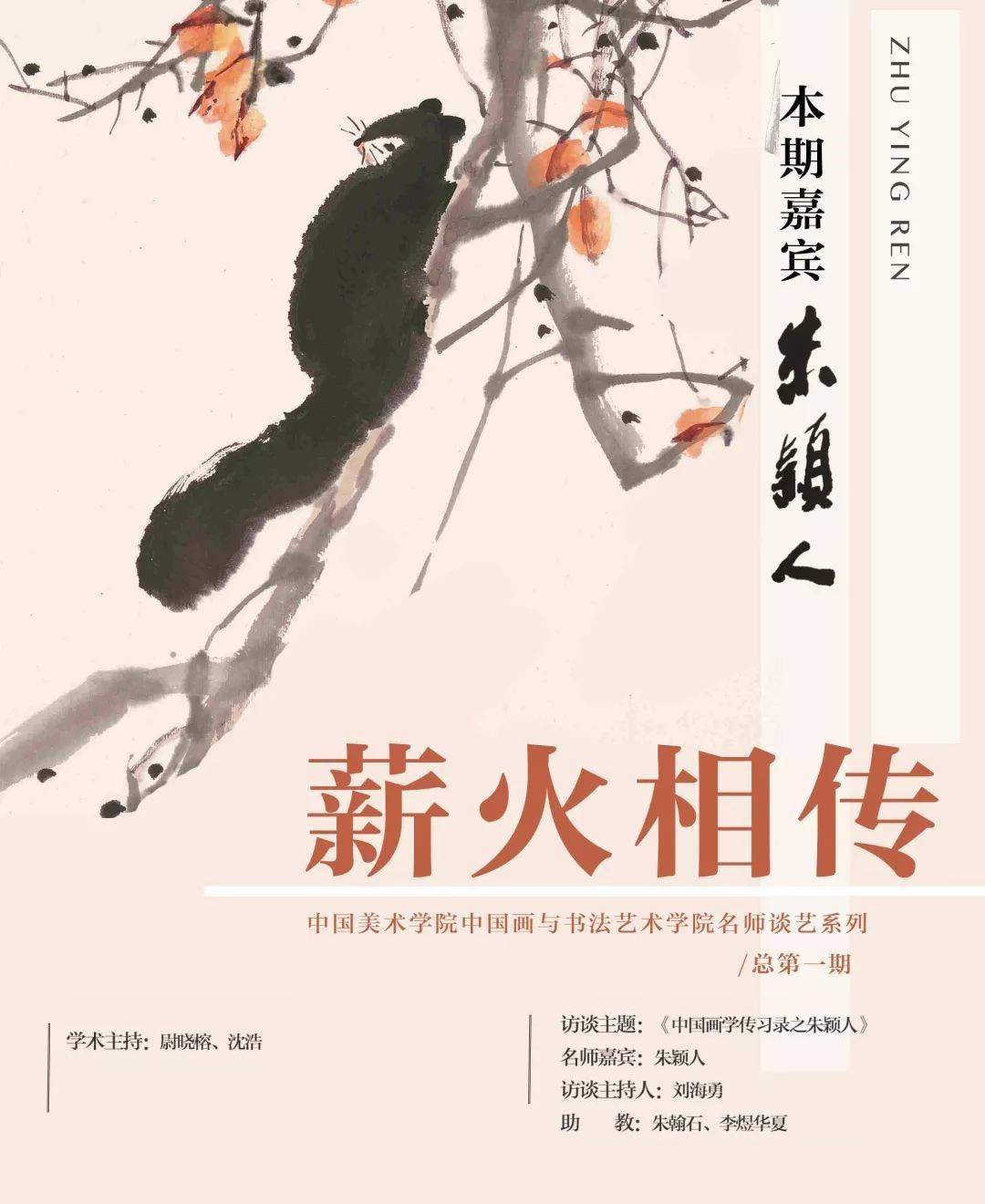
薪火相传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
名师谈艺系列 总第一期
学术主持:尉晓榕 沈浩
名师嘉宾:朱颖人
主持人:刘海勇
1.学艺之路
2. 1959年拜师概述
3.教学与教法
4.《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课徒画稿笔记》的缘起与目的。
5. 写生取材与笔墨关系。
6. 对于当下国画教学的思考。
7. 书法笔法在中国花鸟画法中的转化问题。
8. 工笔与意笔问题
9. 创作与时代气息(答学生问)
10. 朱颖人老师学生田源、顾震岩老师回忆往事
11. 赠书仪式与老师寄语
主持人刘海勇(以下简称刘):建校90年以来,中国画系任教过的老前辈与现在在职的老师们,共同构建了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教育传承的梯队,并逐渐完善了学科体系建设。前辈身上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与创作经验。今天是薪火相传: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名师谈艺系列总第一期,我们将在两年的时间内,对校内的资深教授做系列访谈。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了国画系89岁高龄的朱颖人老师,他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与发扬的。

1.刘:请您谈谈当年考入中国美院以后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朱颖人(以下简称朱):我1947年在苏州美专学习两年,1949年进入中国美院读书,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我最初教的是西洋画,最早指导过的学生是刘文西等,后来去筹办附中并任教。1959年,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时,我参与了当时的主题创作,也完成了其中一些国画的工作,献礼活动结束后,大约得到老先生们的赏识,院领导希望我在中国画领域继续深造。后来,潘天寿先生有感于中国画创作和教学人才的青黄不接,认为应培养新一代中国画创作和教学人才,建议我学习中国画。因为我原本学习的是西洋画,所以我最开始并不是非常愿意学习中国画,只是应师长要求而已。但是,后来在拜师会上,潘天寿先生讲到,拜师会不仅是一个形式,更肩负着把中国传统绘画传承下去的使命,于是我下定决心,深入学习中国画。
潘天寿和吴茀之先生教学都非常认真,但各有特点。潘天寿先生上课、下课都非常准时,但吴茀之先生上课时常会迟到,下课也往往超时,大家观摩吴先生作画,但也耽误了去食堂吃饭的时间,因此经常感到矛盾。老先生们在讲课的时候,有问必答,不仅有课内的指导,还有课外的传授。老师在上课时会认真观看学生作画的过程,及时指出不当之处并进行示范,示范的同时还会由技法本身讲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怎样理解中国画的各种流派。老师不来上课的时候,学生也可以去老师家里拜访,观摩创作。潘天寿先生作画,时常要停下来,从中国画的源流、常识等方面给学生讲评、分析,而吴先生的讲评,涉及的范围会更广。潘先生考虑问题往往从高的角度出发,指出问题的来龙去脉,而吴先生则从深的角度入手,点明问题的内在机理。
学生认真地听讲、理解,准确地把握老师讲课的要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是由西洋画转入中国画的学习,所以课堂听讲、记录笔记都非常认真,课后也对笔记做了整理。课堂笔记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文革时期,老先生们遭受批斗,无法正常教学,靠着笔记的记录,我反复体悟老先生们讲课的精要之处,在创作和教学过程中受益无穷。不同老师看法当然有所不同,但这也有助于我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一个问题,开阔了思路。另外,培养一个画家十分不易,大家在学习、创作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健康,良好的身体对于画家也非常重要。
2刘:中国美院中国画系在1961年举行的拜师仪式,由年轻教员拜年长老师为师,既当学生,又作老师助教,这种方式在当时各大美术院校中绝无仅有。举办这一仪式,学校方面的期望是什么?这种培养方式的要求是什么?
朱:1959年,反右以后,国画系恢复建制,但老先生们大都年事已高,学校担心教师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因此决定在现有老师中间挑选一些人,担任老先生的助教,一边辅助日常教学,一边向老先生学习,以期通过这样的形式培养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教师与学生的双重身份让我感到了一种压力,如果教学质量不高,自己也会很难为情。
教师在生活中要多留意自然的细节,才能在教学中有所依据,课余就在图书馆翻古代书籍与国内外画册,记录有关学习的资料。在生活中仔细观察,强记。例如曾有学生问我鸡的眼皮是朝什么方向翻动,幸好我平时观察留意,才能回答。作为画者,要用画家的眼睛观察自然,记住自然的细节。在写生的时候,看着写生的对象,可以设想一些诗意的情境,然后再去表现自然。
3刘:当时的拜师仪式,是叶尚青先生拜潘天寿先生为师,您拜吴茀之先生为师,刘江先生拜诸乐三先生为师,您们同时也担任他们的助教。您觉得在老先生们和自己的教学中有哪些地方可以与我们分享?
朱:吴茀之先生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受过潘天寿先生的教导,一直与潘天寿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批斗最激烈时,很多夫妻、亲人之间都不敢讲真话,但吴先生和潘先生依然可以推心置腹,知无不言。潘天寿先生受到批判时,吴先生被要求检举揭发,但吴先生只讲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毫不讲违心之言。老先生们的这种人格,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闪光。
潘天寿先生为人耿直,实事求是。有一次我临摹潘先生的画,潘先生看到后直接指出问题,亲自示范。还有一次,我看到农民在田里插秧,想把插秧的场景画下来,但又觉得十分难画,于是请教潘先生。潘先生就提出疑问,说为什么一定要画插的秧?所以说画画的人对对象也要有所选择,适合自己的就画,不适合的就留着考虑。我们在观察自然时,可以找到自己欣赏的东西再画。潘天寿先生还提出,一般书画界都在画的东西,不一定再去重复,因此他的画,题材往往不同俗众。
4刘:您曾编著《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先生的课徒画稿笔记》,1990年初版,现在已印制多版,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请您介绍一下整理三位先生课徒画稿的缘起和目的。
朱:文革后,画坛前辈日渐凋零,有鉴于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整理当年的笔记,让老先生的技法和思想传承下来,这既是一种使命,对我来说又是一种慰藉。退休以后,我花费了两年时间将这本书编纂完成,依照诗、书、画、印四大类将老先生宝贵的见解分类编出。虽然这本书不一定十分完整地记载了老先生们的教诲,但也算是尽自己所能,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朱:这幅《螃蟹》作于70年代,曾被人以为是吴茀之先生画的,一定程度也体现了我曾非常用心地学习吴先生的技法。《大竹海》作于2011年,既用西洋画的观念作中国画,也有传统中国画的观念加入其中。在技法上,既有工笔的画法,也有意笔的手法。先用大笔一层层地画,待墨干后,再用比较干的笔,边调色,边着色,使得山的颜色层次丰富,也符合自然的情形。传统中国画常常是以笔墨在纸面画,而我是先在调色盘边调边画,这是西洋画的方法,但用笔保留了传统中国画的笔法。《螳螂》作于1989年,画面十分简单。我在选择题材时,既从简单的,也从复杂的构图考虑,从中锻炼自己。
5刘:您的作品中松鼠是常用题材,我们想听一听您对中国画取材方面的看法。
朱:其实松鼠不是我最拿手的。通常来说,一些灵敏的东西会比较吸引我。1952年刚毕业时,看到孤山的松树上面,有不少松鼠爬来爬去,它们很灵动、聪明,速度很快,经常观察之下,当时并未想到要画,但对于这些动植物很敏感,感触颇深。后来在南山路的时候,也看到很多松鼠,甚至还有松鼠从树上爬到窗里偷吃东西。曾经有一段时期,我用钢笔素描的方法画了点松鼠的动态与神情,但随后我发现身边也有同学这样画,于是我思考用不同的方法去描绘,就采用水墨的方法来画松鼠。
6刘:您对现在中国画教学有哪些建议?
朱:以前的本科是五年制,在五年里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基础。中国画历史悠久,经验很丰富,例如作画时既有方笔,也有圆笔,方笔、圆笔之间的过渡也是很大学问。作画的方法很多,老师们也各有特色,学的时候,要想清楚老师的特点,避开他们的弱点,汲取他们的优点,走自己的路。当然,在五年时间弄清楚这些问题,是很难的。
我在学画学了几十年才想清楚什么叫笔墨,2010年前后,对一些技法问题又有新的体会,理解到笔墨之中有很多微妙的变化。例如毛笔着纸的轻重变化,运笔速度的变化,转笔和捻管的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等等,思考这些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创作的基本方法。我时常一边思考,一边作画,回过头来一看,又感叹之前走过很多弯路,现在还有很多没有研究清楚的东西。
我还在思考如何将书法的笔法运用到绘画当中。如果不加研究,即便书法写得好,画画的时候也很难体现出来。由书法到绘画,如何运用,其中有很多微妙之处。
作画要注重对比,浓淡、粗细、干湿、曲直、主次等都要很用心经营,用心研究,才能逐渐有所体会。特别是对于情意,这是与个人的修养有关。
潘天寿先生曾经说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画的很好,如果与古人相比,自己就没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因此,每当我画到得意时,都常与古代名作相比较,这样才能进步,否则也只能停留在一般水准,如果自己自满自傲,就难以进步。
故在临摹之后如有所得,要再加以推敲,加深体会。
7刘:请您谈谈如何将书法转化到绘画中?
朱:行笔当取逆势,也就是说笔杆的朝向和行笔的方向是相反的,这样才有力度。笔法中所谓“屋漏痕”、“折钗股”均有强调笔力的意思。屋漏痕,顾名思义就是水在墙壁上流下形成的痕迹。水在流下的时候,一边渗入墙壁,一边往下流动,而且轨迹并全然是直线,这种原理移用到书画之中就是“积点成线”之法,同时在行笔中又有适当的波折。求得浑厚凝重,我是喜欢厚重凝练的一路。作圆笔中锋时,行笔中也当有适当的波动,线条的两边也并不一定要全然相同,例如可以使一边比较匀净,一边有毛涩之感。画工笔有时候要体会写意式用笔的感受,工笔的线质,其实是和写意的线质是一样的,具体可从陈洪绶、颜真卿和晚明书家的用笔中体会。
8刘:当下的中国花鸟画创作,以工笔居多,意笔较少。您对当下的花鸟画创作有哪些思考?
朱:学东西应该广泛,有丰富的取法资源,才能有新意。之所以会出现工笔画多、写意画少的现象,关键在于对形象的观察。工笔易于描补,意笔则一气呵成,对形象的把握要神形兼备,相对更难。工笔容易看到效果,一般人也会喜欢。同时,一般人对中国画的内涵,对中国传统的笔法理解较浅,意笔画既要考虑造型,还要考虑笔法,很多人理解不到其中的内涵。
如果横向比较,我校学生的传统功底还是不错的,但如果纵向比较,总体水平还是过去好一些,当然现在也有个别佳作。可能现在的创作者对自己创作的追求有所懈怠,例如人物画,文化大革命前,浙派人物画就比现在的好,现在的人物画,面部晦暗,像没有洗过脸。
9刘:请您谈谈花鸟画如何反应时代气息的问题?
朱:文化大革命中,我曾与马其宽先生创作过许多革命题材的画作,但现在看是失败的。强行融入是行不通的,还是要首先欣赏自然中美的东西,再由自己灵魂深处去体会,将体会得到这些的美表现在画中,作品也才有存在价值。如果作品无法让观众感动,那也是失败的。
10刘:2004年之前,我院花鸟画方向招生的专业考试内容为写生、创作、书法,作画工具全为毛笔,2005年招生考试方法进行了调整,每年招15名,8名为传统的毛笔考法,7名为硬笔考法(素描、速写、人物半身像线描,作画工具全为铅笔或炭笔),这样的招考改革已经实行了十余年,您对这种改革有哪些建议?
朱:我本身是画素描画油画出身,素描对形象准确性的要求以及色彩冷暖的变化令我受益匪浅,如果学生善于在思想上加以转化,那么中西绘画的融合是容易的,如果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则这种融合会很难。这一转化的核心在于要理解中国画更侧重精神上的准确,而西洋画则侧重于形象方面的准确。

学生提问:
学生问:朱老师,您好!我们现在学习国画,大都先从某种特定的笔墨语言开始建立对技法的理解,进而形成一个个画面。但如果从创作的角度出发,将各种各样的题材用这种已经形成的技法和笔墨去表现就觉得很困难。所以想请问朱老师,如何将各类不同的题材内化为自己的笔墨,如何将时代精神转化到自己的创作中?
朱:潘天寿先生讲过,在学校的学习目的就是打基础,搞创作则是走出校门,踏入社会之后的事情。对一个事物,要有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不能依靠别人教给你固定的方法,而在于自己思想上真正的领悟。在创作中,要体会到入画的对象好在什么地方,用某种方法去表现,是否能被观众理解,这些问题都是要以自己为主,而不是套用既定的方法或程式。
田源(中国画系副教授、原花鸟工作室主任):我们作为学生对朱颖人老师十分敬重,当年我的毕业创作就是朱颖人老师指导的,当时朱老师来授课时都是非常认真负责,朱老师每次都是准时到教室上课。包括下乡写生的时候,朱老师对于学生们的衣食住行都考虑地十分周到。朱老师对于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是国画系教学中一个非常好的典范。所以老先生身上的优良品质需要通过我们一代代去传承下去。
顾震岩(中国画系副教授、原中国画系副主任):朱颖人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到现在也深深记得在当年毕业创作的时候,朱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传统的东西要做好。因为我当时的创作在构图构思上有一些新潮,以及参加一些新派展览。但是我一直谨记朱老师的这句话。所以若干年后,我立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传统的研究。所以我在这里十分感谢朱老师当年对我的提携以及为我指明了艺术发展方向。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希望同学们能够珍惜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学习机会。
扫描下方二维码
加入免费课程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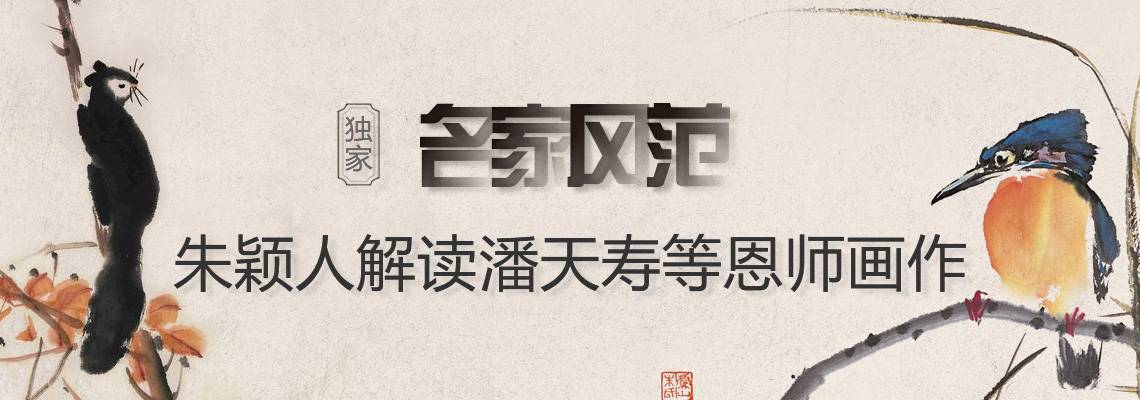

美术名家课堂
服务项目:美术视频教学、名家约课、名家直播、美术热点等
官方网站:www.msmjkt.com
联系方式:0571-85310917
商务合作:0571-85310901
联系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浙江日报文化产业大楼24楼
文章来源: 国书院学生会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