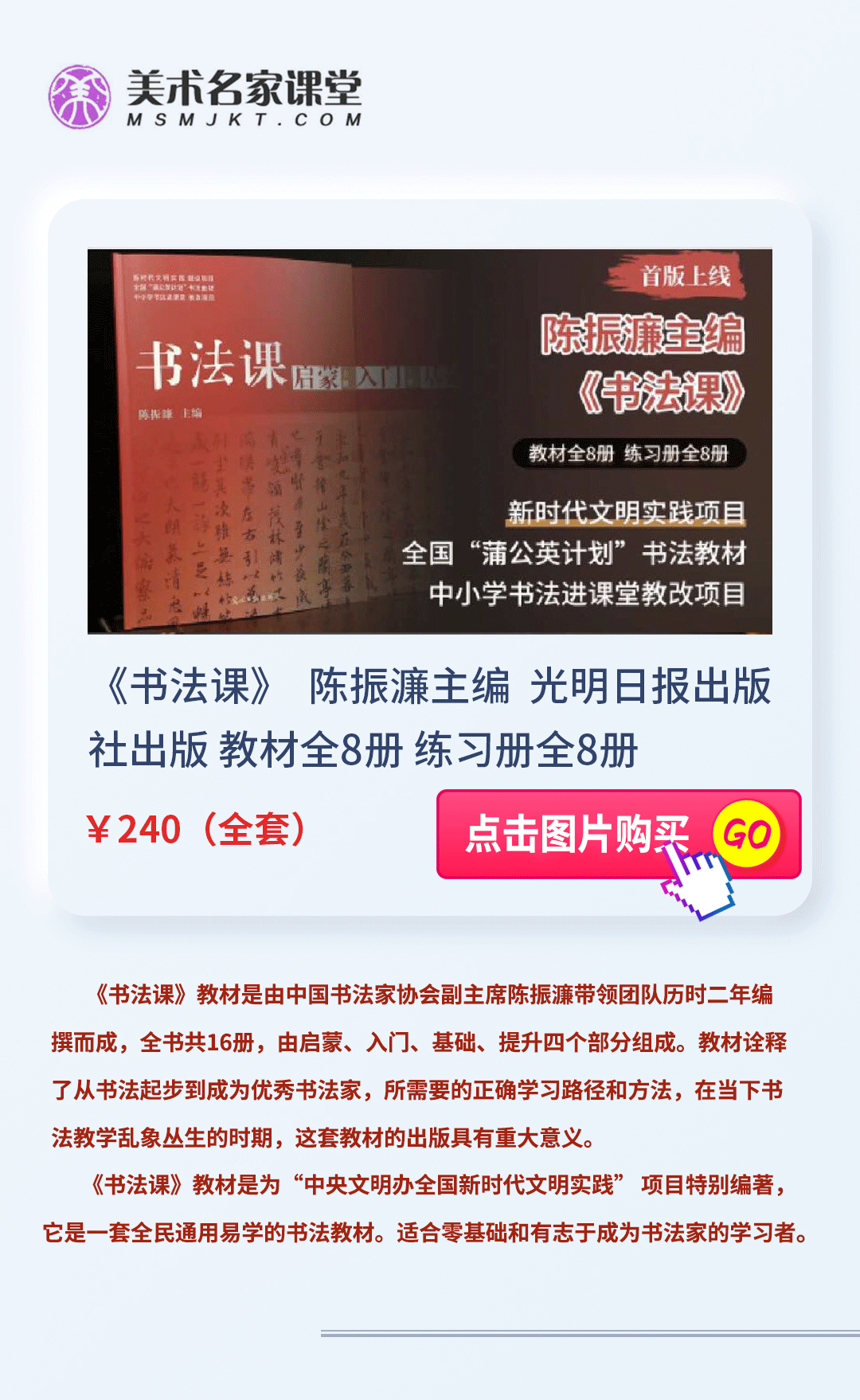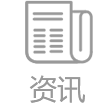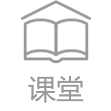今年是蔡元培先生逝世80周年。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强劲外来文化冲击下的二十世纪初开风气之先,提出了包括“五育并举”“以美育代宗教”在内的众多理论命题,责无旁贷地扛起了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旗帜。弹指间,沧桑百年。百年来,对“以美育代宗教”的讨论从未停止,这一美学命题历经了哪些实践?又能为当代中国提供怎样的精神补给?

蔡元培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其身后,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无力偿还,就连入殓的衣衾棺材,也是弟子王云五代筹而来。30多年后的初夏,蔡元培下葬的香港公墓接到一通电话,来电问:“蔡元培先生的墓地在哪儿?”守墓人显然不知道蔡元培是谁,几经追问才犹豫地回答:“也许,你们是在找‘蔡老师’的墓吧?”荒烟蔓草中,诗人余光中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那一方高不及人的墓碑,上面只有七个字——蔡孑民先生之墓。感慨万分的诗人不禁留下了“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的诗句。
与蔡元培先生携家人到香港时的仓皇与略显凄凉的晚年景况不同,在其逝世后,内地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与追悼大会,并有多种纪念专刊出版,甚至在1940年3月24日全国寄出的信件上,都盖上了一枚特殊的邮戳: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与蔡元培生前亦学亦政的经历相对应,纪念仪式的出席者亦往往拥有多重身份,但无论何党何派,都发表了悼念蔡元培先生的挽联、悼词与评论,人们用的最多的两个词,一个是“楷模”,一个是“完人”。
就是这样一位学识才情与时代要求相契合的“楷模”“完人”,蔡元培先生不仅真正全面开启了中国的百年美育之路,还给中国美育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发轫
1908年,40岁的蔡元培正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注册,在学籍卡上,蔡元培填写的年龄却是35岁,因为他生怕德国教授会因为自己年纪太大而拒绝他入学。这张年代超过一个世纪的学籍卡,迄今仍保留在莱比锡大学档案馆里,它见证了一位中国学者孜孜不倦、焚膏继晷的勇气和毅力,也见证了近代中国努力向西方寻求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艰辛历程。蔡元培晚年回忆起这段求学经历时说:“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须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自此,美育成为蔡元培一生的学术主张。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时代漩涡之中。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中国社会逐渐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新民”与“强国”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而教育也被视为文化变革和社会革新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教育开始了现代转型,美育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早在辛亥革命前,蔡元培就坚决反对清政府“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辛亥革命后,伴随复辟倒退的政治走向,思想界尊孔读经的取向复燃。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针对清政府忠君、尊孔的钦定教育宗旨,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思想主张。蔡元培所说的“美感教育”,也就是审美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他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即通过美感教育与智育相辅而行,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以期达到一种高尚、完善的精神境界。
“以美育代宗教”的时代浪潮
1917年4月8日,此时已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应北京神州学会之邀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说”的专题演讲。随后,这篇演讲词以《以美育代宗教说》为题先后载于《新青年》第3卷第6号和《学艺》杂志第l卷第2号。五四运动前夜,“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一经提出,仿佛一块巨石落进了原本波澜不惊的湖面,在教育界和文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提出,是建立在康德美学之上的,他特别强调康德认为美有“超越性”与“普遍性”的理念。蔡元培认为“自兄弟观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之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智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
北京大学教授丁宁认为:“当时,我国的宗教与其他宗教不同,更多偏重于实用性的目的,而不是一种纯精神的追求。而蔡元培的美育理念是无功利性的,是改造国民性的一种特殊途径和有效过程。”蔡元培在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呼吁人们不能忘记美育,既要“实施科学教育”,又要普及美术教育,以培养人们活泼高尚的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神州学会的演讲中,蔡元培说道:“我说美育,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之后,可以休了。”从此,对于美育的孜孜以求成为他毕生的功课,直到逝世的前两年,他还在为未能以《以美育代宗教》为题撰写专著而深感遗憾:“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是憾事。”而以蔡元培当时的地位,他对于“以美育代宗教”的提倡,堪称振臂一呼,随即应者如云。无疑,百年中国持续发酵的美育热潮由此开启,而蔡元培功莫大焉。
文化建构中的美育与实践
“五四”是一个价值重构的时代,而在这一过程中,美育无疑扮演了主体性角色。彼时,蔡元培提出的救世方案“以美育代宗教”连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旨一道,使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重要战略堡垒。而在新文化体系中,美育之所以被提升至宗教的位置,不仅因为它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所具有的启蒙价值,更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向。蔡元培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将美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以陶养学生的健全人格。1917年末,他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并设立“画法研究所”,蔡元培亲任所长,聘请陈衡恪、贺屡之、冯祖荀、徐悲鸿、钱稻孙等绘画名家任导师,并亲笔题写会刊《绘学杂志》刊名。此后,“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北京大学造型美术研究会”等研究会相继成立。
北京大学文科的国文门、英国文学门和哲学门在1918年开设了《美学》课。三年后,由于没有任课教师,蔡元培亲自上阵讲课,这也成为他主持北大期间亲自开设讲授的唯一课程,上课的学生挤满了可容一两百人的大教室,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可见几年下来提倡美育、开展美育工作的成果。而这皆与蔡元培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同时又敏锐地意识到美学在这个时代的特定价值与作用有关,这无论对北京大学,还是对当时之中国来说,无疑都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首都师范大学美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德胜在采访中谈道:“美育与一般知识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强调通过日复一日的浸润式熏陶来持续滋养人的个体心灵意识自觉,因而美育在总体上不是一套完整的‘知识话语’,而是一种实践性存在,其主要是通过兴办艺术院校,推广学院教育而展开的。”
1918年,蔡元培参与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创办。开学式上,蔡元培发表演说,指出因经费不敷之故,本校暂设绘画、图案二科,将来经费扩张时再增设书法、雕刻等科目。他对郑锦、林风眠、徐悲鸿等早期的校长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一年后,上海美专成立校董会,由蔡元培出任主席,主导革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并任命梁启超、袁希涛、沈恩孚、黄炎培为校董。
1927年1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采纳艺术教育委员会建议通过了《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倡议择址杭州西湖。1928年4月9日,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在西湖孤山南麓罗苑举行开学典礼,林风眠为首任院长,林文铮为首任教务长。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中指出:“西湖之滨的自然美与人造美同样需要;艺术与科学一样重要;大学院设立艺术院,纯粹为提倡此种无私的美的创造精神;艺术院不在学生多少,而在能创造。”
2018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期间,校内师生特意创作了《国美春秋》四联巨幅油画,第一幅《清明》就是为怀念创建学校的第一代先师而作,而处于画面中间坐在石头上的长者就是蔡元培。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在采访中特意提到:“中国美术学院的缔造者就是蔡元培先生,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的思想深深地浸润着我们学校,成为我们始终如一的精神核心。他高度重视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教育,这启示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应把社会美育作为我们学校育人的根本使命,我们在其影响下衍生出艺理兼通的哲匠思想和湖山人文的诗性精神。他还强调学术研究,视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我们继承他的衣钵,同样强调高校对高尚学问的研究。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重师长、崇尚个性,培养了一代代精英。”
蔡元培美育理念的当代探索
蔡元培毕生提倡美育,始终奔走于教育和革命事业中,通过实践,不断普及美育理论,最终确立了美育在我国现代教育领域的重要地位。王德胜谈道:“站在现代中国文化精神重塑的角度来看,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主张内含着一种特定的思想建构模式,这就是突出强调了价值信仰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特殊地位,突出强调了人的精神改造对于整个社会改造的深刻意义,突出强调了人生长远发展和现实生活中需要具备真正有力的精神纯化能力。这就意味着,‘以美育代宗教’其实不限于美学或美育层面的意义,应该把它放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需求的层面上,视其为一种功能性的文化建构观念来理解其特定价值。”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重要论述,“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讲话中强调的“构建德智体美劳培养体系、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等要求,指明了美育是实现教育目标,培养全面完整的个体的必要途径。
“百年过去了,‘以美育代宗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社会美育’等理念,我们仍然在坚守和实践。更重要的是,当代对其已经有了新的、更深的要求。比如我们今天谈‘以美育代宗教’,已经不是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民族救亡的背景下展开,而是在中国全面实现小康、实现文化振兴的背景下来实践。所以我们今天谈社会美育,不仅仅是要培养几个艺术家、画几张画,而是希望我们全社会能够通过美育形成一种饱满的中国精神,形成一种丰厚的中国式审美,把这种精神、这种审美变成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来回馈世界,塑造中国人的形象。就眼下我们正经历的抗击疫情来说,多少‘逆行者’在一线扎扎实实地工作,这其实就是社会美育需要的核心精神,我们艺术工作者怎样将这种精神提炼出来,用怎样的热情与笔墨创作艺术作品,就是我们今天践行社会美育、深化艺术研究,以美育力量回馈社会,需要面对的挑战与义不容辞的责任。”许江院长在采访中进一步谈道。
百年间,国内对“以美育代宗教”命题的研究与实践从未间断,但是严格说来,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只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主张,而不是一种详细论证的学说,因此从它作为一种理论或者学说来讲,确实也存在着些许时代局限性,但是,却也因此而堪称一个完美的开始,一个可以永远“接着说”的开始。为此,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甄巍表示,“重读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尤其能够体会到美育的核心价值在于育人。艺术教育中审美能力的提升,是人与外在世界交流中‘带有美的感情的具体体现’。无论是因感而情或因情而感的感兴,抑或有感而发、迁想妙得的创造,完整人格的养成和生命幸福的达成,一定是在审美过程中才能实现的真实与自由的状态。”
相比他身后群星闪耀的中国学术黄金时代,蔡元培人生的最后几年,几乎是潦倒晦暗,直到逝世,他都没有一处自己的房产,但就算这样,在弥留之际,他仍然模模糊糊留下一句遗言:“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想必,这就是这位“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留给我们后世最真挚、最殷切的期待。
而今天我们对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学术主张的还原性重构与反思,对中国现代美育百年发展的回溯,不仅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重新领略了“美育”的文化导向与精神诉求,也让我们在历史所赋予的足够的距离中,感受到了“以美育代宗教”的时代局限性与新的可能。换言之,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主张所拥有的精神价值与历史遗训,始终是中国美育建构的理论支点,也必将是未来中国美育发展必须尊重的历史坐标。这些持续言说与探索,也许就是我们对蔡元培先生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