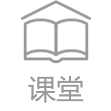从“师徒制”到“学院派”
专家学者研讨新语境下的花鸟画科教学
■本报记者 江凌 通讯员 刘杨 刘元玺 张靓亮
|
韩璐 上善若水 60×95cm 2014年
|
|
刘海勇 秋雨亦如酥 198×98cm 2016年 |
编者按:
花鸟画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方向被正式确立,是从1961年开始的。是年4月,时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赴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应该分科学习的意见。之后,文化部同意在浙江美术学院率先进行中国画分科教学试点,并适时将这种分科教学的方式向全国各大美术院校推广。
中国画分科教学是在中国画教与学问题上进行的一次大胆的教学改革,是通过缜密思维与反复探究后的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尝试。伴随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也随之有着不同的时代坐标与文化担当。艺术的多样性发展态势和文化的多元化存在趋势,给予中国画在人才培养上更加宽泛的价值取向和更加灵活的方式方法。
3月10日,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画语诠·新语境”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教学与研创论坛系列学术活动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此次系列学术活动由三展一会组成:“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在职教师作品交流展”、“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文献及系藏花鸟画教学范本展”、“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经典教材之卢坤峰《墨兰说》示范图例展”,以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花鸟画教学与研创学术研讨会。
该活动希望从专业发展的侧面反映中国画在传播过程当中的现状,使中国画艺术教育在历史推进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开展文化创造与创新,全面推进中国艺术教育和中国画学科繁荣发展。
本期,美术报节选本次研讨会的部分观点,聚焦当下花鸟画的教学、创作等问题。
薛永年:
以开放的态度调整观念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花鸟画产生比较早,我发现最早的一幅是美国艾金斯博物馆收藏的汉代作品,画面中一群乌鸦在树上飞。魏晋就已有花鸟画的名家,到了徐熙、黄筌就完全成熟了。西方也有类似的花鸟画,比如说后期印象派梵·高的《鸢尾花》,它与扬州八怪李鱓的《蝴蝶花》题材一样,但追求就全然不同。梵·高的《鸢尾花》画于他的生命后期,他是要画出生命的辉煌和旺盛的活力;而李鱓的《蝴蝶花》,是他被迫离开宫廷画师的岗位、流落在民间之后,在一个春雨季节看到了农家土墙头开得像紫云一样的蝴蝶花,画了这张画,还提了诗,从画和诗的结合可以看出不仅是要表现一种生命,更是通过蝴蝶花想到了庄周的梦蝶,他要发挥自由的创作精神,想要大胆突破一些束缚,画中所表达的东西比梵·高多了一些。再如莫奈的《睡莲》和金农的《莲塘图》。莫奈的睡莲是要表现天光水色的丰富多变;而金农是杭州人,但是活动在扬州,他带着一种乡愁,画六月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他不满足于画河塘,还画了一只船,通过船来表达画外的东西,虽然画中没有人,但可以感到“衣香鬓影、丝竹管弦”,传达给我们的内涵比天光水色要多。
花鸟画有一个重要传统是寓兴,“寓兴于象中”。徐渭的《墨葡萄》体现了寓兴的传统,其中有一句题诗,把“葡萄”比喻成“明珠”,一开始我看不明白,怎么葡萄画得像藤萝,后来我慢慢看,他画的是葡萄干,没有采摘,已经晒干了,表达一种无法排遣的悲愤。徐渭的《石榴》,石榴在山里已经成熟了,但是没有人采摘,跟野葡萄一个含义,来寄托他的感受。
我们看齐白石的作品《荷花影》是上世纪50年代初被王朝闻先生发现的,他评论这幅荷花画得绝了,这个影子画正了,如果水面上有波纹,那个影子应该是散落的,他画的影子一点都不散落,而且一群蝌蚪在追逐影子,你在岸上通过光线的折射才能看到倒影,而蝌蚪在水里根本看不到,所以齐白石画的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一种艺术想象,不是画“有”的东西,是画“没有”的东西。水里的荷花影子美不美?美;小蝌蚪执着地追逐影子的精神好不好?好,但是如果追逐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那不是白费吗?这就是深刻的生活哲理。
再谈形的迁想妙得。郑板桥的《兰蕙瓦盆图》,把兰花画得满天飞舞,题了一首诗,所有的君子都要找一个岗位,岗位不够就互相拥挤,他说我不去争名夺利,喝酒就是了,画一个酒缸。安徽宣城梅翀的《松芝图》,松树同时还能看作是山,山上长了植被,双重的利用形的相似来加强含义。
清代李方膺的《潇湘风竹图》,不仅画了飞沙走石,而且画出了风,该画可以听到声音,这是他在题诗里讲的。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以前我们认为完全是齐老先生独立创作的,前几年北京画院公布了一个材料,就是老舍向齐白石求画的那封信,才知道这张画是两人的合作,老舍的信里面“蛙声十里出山泉,查初白句。蝌蚪四五,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想矣”。钱钟书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谈了通感,感官之间的感觉是可以沟通的,当我们在看画的时候不只在看,也在闻,也在听,甚至还在触摸,从一个角度表现,在人们心目中唤起的是通感,这样才能有了完整生动的感受。
最后讲象外之意。齐白石的《二三子》,两只小鸡争蚯蚓,还有一只小鸡看着。后来我们发现一张画,是齐白石给他第三个儿子画的,画着老公鸡和小鸡,大概老公鸡象征齐白石自己,他在题跋里面讲到了鸡有五德。见到好吃的不吃独食,要把它的兄弟姐妹召唤过来一起吃,有团队精神、集体精神。但是齐白石看到的不是如此,他对古代的传统做了重新解读,说小鸡需要教育和历练,这种仁德是将来可以具备的。齐白石的画不仅是笔墨好,还有一些很深刻的思想,是从生活当中体悟出来的哲理,而他对文化积淀的使用是批判和重新阐释的。
齐白石的《盘蜂》,这张画好在哪里?是因为工写结合,还是构图巧妙,每一个圆形都被破掉了,我想可能都不是。齐白石的出名离不开陈师曾,他在中国绘画史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宋宣宗的时候设立画学,就出了题目,一个题目就叫“踏花归去马蹄香”,还是涉及到通感问题,有一个画家画得特别妙,画蝴蝶追逐马蹄,就表现出马蹄香,通过形来表现嗅觉,把诗意呈现,获得了奖励。齐白石这幅画在我看来,是在古代历史故事的影响下,接受了通感的传统,蜜蜂没有飞来之前可能有鱼有虾,所以它来寻找了,让我们创作者能够用非常少的笔墨来体现更多的耐人寻味的东西,不仅要“象”,而且要有“象外意”。
在花鸟画的宝贵传统里,有些内涵还是有待于进一步挖掘的。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调整观念,以西方思维进行中国画问题的判断。

陈平 梦剪清绡一半来(局部) 30×1500cm 2007年
于洋:
从万物的角度看花鸟画范畴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教授)
当我们今天站在时代坐标时再回看20世纪的花鸟画,尤其是近现代的塑形过程,会发现其实花鸟画从艺术本体的现代程度来说实际上最深入。回看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家,三位都是花鸟画大家,花鸟画创作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实花鸟画在古代传统里面形成了格物传统,经常被认为是玄虚精神的发源,对物与我的反思。这样的一种认识,包括我们以往对写意的认识,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一个巨大的靶子。今天,对于学院式的、写意式的教育存在当代焦虑,究竟能否进入到现代形态和当代形态,尤其是当代艺术大的国际化的中西交流的格局里面。在大的中西绘画体系的对照之中,写意花鸟画的活力在今天有被激发的更好可能。
传统的花鸟画传承方式是注重人格的、志于道路的,但是在20世纪变成了全科式的体系性的学院教学,由传统意义上的私塾性的画谱式的教育往现代学院教育。古代传统花鸟画的技法观念在20世纪上半叶以后,实际一直是占据主流的,从传统的私塾的传授一直到现代学院的调试,当然也涉及到文雅与通俗、临摹与写生、笔墨与造型等等关系的问题。
其实从传统画谱到今天的花鸟画画学的建立,这里面有一个提升的问题,背后也有我们对于花鸟画画科的反思,我也听到其他有些声音,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讲人物、山水、花鸟的划科”,甚至于中国画这样的词在很多场合被当代水墨这个词所取代。如果我们在一个大格局里面看,花鸟画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如果用“万物”这个词,我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徐渭,无定式地泼墨于纸上而形成了岩石与花草,所以他的笔法体现了极度的放任洒脱,而且似乎从未事先规划细节,但是同时又指出徐渭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利用了构图和笔法的这种模建体系,试图用一种模建体系来讲述东方传统对于万物的表达。其实这背后也使我们反思,这种局部式的、相对化的自由和个性,源于变异的寻常和变化中的不变,这也是我们今天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花鸟画,从万物的角度来看范畴。
我们从原有的花鸟画理法的教学到今天学院式、全科式的教学,作为学科的立体性,更重要的是召唤实践和理论的进一步结合研究,当然也包括展览形态的研究。我们今天呼唤学者型的画家,反过来我们也更需要画家型的学者,或者说对于艺术本体更有解悟的,对于艺术作品的技法理法更有渗透感知的学者,而不是从一个文献性的角度或者从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套用解释。
林木:
以中国式思维去观察
(林木: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
中国画的创造应该是一种中国画的思维,中国画的思维是意象式的思维,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思维。落实到具体是一种包括观察、选择和表达的思维方式。比如说空间思维,宗白华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专论过,他认为是中国人的一种“仰观于天、俯察于地”的宇宙空间意识,这种空间意识是一种“俯仰于天地宇宙之间”的远的心灵空间,这是中国人的空间意识。如果仔细看董其昌的山水画,前后都是清楚的,没有什么近浓远淡,有时候远处还要浓一些,中国人希望看到什么就把什么表现得很清楚。沈括就说前山后山都要看完,最后把天地万物归纳到心灵之中,所以我把这个空间称之为“心灵的空间”或者“灵的空间”。
具体一点来说,我觉得写生中也有一种中国式的思维,应该叫笔墨思维。笔墨思维是一种中国画的语言思维。我们在写生中首先要观察,用什么方式去观察?画中国画的人,应该在客观场景当中看出平面的、虚拟的、黑白的、大小的、清晰模糊的关系,在看对象的时候用中国式的方式去处理,具备中国画的社会方式。在对象中看到一幅笔墨精彩的中国画出现的时候,才是我们提笔写生的时候。这就涉及到写生作品的选择问题,不是任何看上去好看的场景和适合拍照的对象都适合中国画的写生,对象的正确选择是成功的一半,或者对对象细节做选择也都是写生与非理想对象式的一种补救和完善。
还有一点是表达中的思维。不是如何用笔墨去表达对象,而是让客观对象如何转化成画面中主观处理的笔墨,非此而不能形成一幅中国画意味较强的中国画。观察现实直接提炼成笔墨,如白描的线条提炼、山水云雾的笔法墨法的提炼,或具有笔墨指法的提炼,或突破既有笔墨创造笔墨新的意味,只有立足于现实才有无穷无尽的笔墨想象、提炼和再创造的基础,这是何以要外师造化的缘由。如不去做笔墨的主观倾向的提炼和再创造,我们也不可能中得心源。
张立辰:
花鸟画要按自身规律发展
(张立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花鸟画是中国画中很重要的一个学科,它的重要性在于花鸟画的地位从独立成为学科之后,虽然有所争论,但是在传统的观念基础上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创新,所以在整个绘画艺术当中是很惹人注目的一朵奇花。潘天寿先生在1963年明确提出了中西绘画拉开距离,这并不是一种保守的观念。这个理论在当时东西文化之争的情况下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中国画能否按照自身规律发展。这个观念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整个美术界和美术教育中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重视程度,这点也是我一直在忧虑的。
各个方面的干扰和新思潮不断迭起,整个文化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诸多问题,对中国画的传统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画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和坚强的,生命力来自于中国文化的多种元素的综合,中国画已经走向了它自己的现代,这个现代指的是什么?这个现代因素是什么?如何走进现代?这个认识大家并不完全相同,往往一提起现代就想到西方。西方是西方的现代,中国是中国的现代,这两个概念不要混淆。我们在教学和创作当中所思考的问题都离不开本民族的传统基因,尤其是现代也离不开中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也是一个现实。有些人就主张自由发展,好就发展,不好就灭亡,实际上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时代的潮流有的时候是合理的,有的时候是不合理的。
去年我听到这样一个观点,文化像流水一样,哪里低往哪里流。我说不对,文化不是这样。西方的强势文化向世界一些古老的文明古国流过去了,这是高的东西流向低处吗?不是,不一定以高低而论。我到过埃及,也到过两河流域,也到过巴基斯坦,他们的传统基因现在很少看到,到他们的高等院校里看,原来的古代绘画都不太见到了,这个现象难道也是流水的道理?高处向低处流?我觉得不是。中国文化底蕴太深厚,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式不是阶段性的。中国是积淀式的发展,我们的前人根据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不断地积累形成现在的文化宝库,所以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应该有自己的发展规律。
《艺术的终结》这本书基本还是有道理的,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艺术的终结》不代表世界的艺术,更不代表中国的艺术,主要指西方艺术的架上艺术。而中国画恰恰不同,中国画吸收其他艺术是很正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西方艺术到了中国,或者中国人到了西方看到西方的东西,自然会考虑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别和共性,必然会考虑到东西方艺术各自存在的问题以及它要往前走所需求的资源。中国文化一方面不拒绝吸收其他,但是主要的生长点还是来自于传统文化的丰富基因。
诗书画印合流以后,以写意画为代表的花鸟画家标志着中国写意意向体系走向了现代,这点是非常清楚的,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画的发展更说明了这一点。现在从美术教育来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承载传统文化发展任务的教育阵地。各大院校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在教学上实施了很多新的举措,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都争取能够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多承载一点传统文化的基因,不要让它转基因。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像浙派人物画就是改造和反改造的结果,浙派人物画的代表人物都在中国画人物画笔墨的变化和艺术表现方面作探索,这个成果来之不易。中西文化矛盾重重,很不容易走到现代,我们应该珍视这些经验教训,今后走一个更理想的路子,使得中国画健康地发展。

黄芳 一庭花影 33.5×32cm 绢本设色 2016年
姜宝林:
中国画应该姓“中”
(姜宝林: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咱们中国画应该姓“中”,应该有我们民族的独立特点,才能屹立于世界。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往往用西方的艺术理论来解释中国画,甚至用西方翻译过来的词汇,来代替中国画理论和题跋里面常用的一些中国特有词汇。举个例子,我经常听到我们在国画领域里面用“造型”的词汇,我个人理解,“造”字有一种塑造刻画的意思,用在西画里面是符合西画的创作规律的,因为油画、素描的形象要反复地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但是中国画是写意,它不存在造型,下笔就有“形”,所以这个“形”不是塑造出来的,是写出来的。我觉得“造型”这个词汇用在中国画里面不恰当,我们是下笔就有“身”,有“身”就有“心”,身寄托在心上,身本身就是写出来的,我个人觉得“造型”是否可以用“写形”来代替,潘天寿院长用的是“捉形”。这些小地方应该拨乱反正,不应该用西方的美学或者西方的艺术规律以及理论来解释中国画,应该是沿着中国本身的本体思维往前推进、往前演变,推动我们的创作。
文章来源: 美术报
原文链接: 点击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