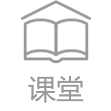地上繁忙,地下沸腾,我们常常听到矿区遇难的消息,煤灰一层层落,矿灯晃晃入目光,战在地下一线的工人们,与阴冷潮湿为伴,用汗水与生命换来乌金墨玉,是井巷的逆行者,也是光与火的采集者。
-
故事1:一件毛衣的故事
-
故事2:连长矿工
-
故事3:不见了的马强
-
故事4:见到三班组了吗
一件毛衣的故事
某年,夏天,陕西某矿场。
北方的夏天,到了中午就异常炎热,烈日当空,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太阳把工地烤的滚烫,行走间晒得干裂的石子在路面滚动,在上面画画的我们只着一件T恤,也热的汗流浃背。
相反,矿井底下非常寒冷,矿工们下去得穿两层棉袄。

升井了,上来一个矿工,黝黑黝黑的煤渍糊满了脸,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经过整晚的工作,掩不住的倦色,身上的棉袄湿漉漉的,看着十分厚重。开始画的时候,我提议让他脱掉外衣,他不肯,操着一口浓浓的北方口音说不热不热,你们画吧。递给他水,他也不喝,我不敢多说,只好赶紧开工抓紧时间画,生怕耽误他休息时间。

起完形,刚把画框铺平准备上色,一抬头就看到矿工脸色不对,青紫青紫的脸庞,眼看着身体往后一仰要倒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不好!中暑了。赶紧冲过去抱住他,掐人中,灌水,洗脸,尽快给他散热,脱去了厚重的棉装,露出了里面的毛衣——一件深绿色的毛衣,由于长期在井下工作,上面积满了灰,从袖口到领口到处都是洞。
不一会他醒了,醒来以后赶忙说:“没关系,你们画你们画。”我们就和他说我们已经画完了,实际上并没有,催促着让他赶紧下楼洗澡。
隔了一两天,当我再次碰到这个矿工的时候,我问他穿的毛衣是多大的,他敏感的回绝了我:我不要毛衣,我有的。你不用问这个我知道的,谢谢你。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景渐渐远去,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矿工兄弟绝不希望麻烦任何人,他们把所有的苦都暗自咽下,而那件绿色毛衣也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
后来我常和同学们说,要想把矿工画好你得变成他,变成他你才能画好他。
连长矿工
2020年末的时候,我去了山西的一个矿场。
和以往不同,这次见到的矿工都戴着眼睛,和我聊天间,问出来的问题让我意识到他们是有文化的人。我问他们,你们读过大学吗?其中一个矿工坦率地说:“当然!我读过大学,我大学还是本科的!”自此以后我每画一个人都会问一句,发现他们几乎都读过大学,这使我非常吃惊,在我十余年的矿工绘画中,是鲜少的。其中有一个矿工是安徽某所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当了海军,一路做到了连长,在舰艇上工作了好几年,回来后就到这个矿场当了矿工,如今已是矿区掘进队的小队长——那是矿场里最艰苦的一群矿工,战在矿场的最前线,是名副其实的冲锋队。


邀请他配合作画时,发现他并不瘦,相反还有点胖,请他坐下,他忙摆手说坐不了,坐不了。后来拗不过我们,靠着墙,直着腿缓缓移动着身子这才终于坐下了,他的膝盖受过伤,我心想,一问,他拍了拍膝盖:“在矿工工作啊和在部队一样,每一个工种都得密切配合,有一次矿里出了点小问题,作为一线掘进队的队长,在井下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长时间的泡水,再加上膝盖本就划伤,自那以后,这膝盖啊就不行咯!”他笑着回忆着往昔,仿佛这不并是什么大事,而我们心中都清楚,谁又真的能想象在长达16个小时的漫长黑暗中是如何跨过那一分一秒,克服心中恐惧呢?

《掘进队矿工韩志红》,纸本水彩,105x75cm,2020年

《矿工芦卫东》,纸本水彩,105x75cm,2020年
我问他,怎么读过大学当过连长还来矿区当矿工,他笑着说,我父亲也是这个矿的,一干就是几十年,我们一家人都和这个矿有缘,所以我就回来了。两代人的情缘,而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更多我们说不出,道不清姓名的人在这里,与月相伴,与煤同眠,耗尽几代人的心血开采着。
后来在画的时候,每画一个我都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真名真姓,是最朴实无华的名字,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鲜活劳动者的印记。

《矿工杨霖》,纸本水彩,105x75cm,2020年

《矿工智伟》,纸本水彩,105x75cm,2020年

《矿工芦建国》,纸本水彩,105x75cm,2020年
不见了的马强

矿工 马强
画过那么多矿工,但要说记忆最深的那就是马强了。
7年前,我去画过马强,7年后,我又去了。
7年前,我写了篇文章叫马强不见了,7年后我又写了篇文章叫马强找到了。
那是在山西的一个矿场。天还蒙蒙亮,北方的冬天早上一片迷蒙,整个矿产笼罩在薄雾中,飒飒的西北风吹着,即使穿了厚重的棉大衣也抵挡不住寒气,空气中飘散着细小的雪粒子,拍在脸上,我们蹲在井口抱团取暖。到了凌晨6:30正是升井的时候,我站起身,捂了捂冻的发僵的脸,静静等待。一群矿工升了上来,浑身黑油油的,头戴钢盔,手拎矿灯,就像是战场凯旋归来的战士一样,每个人的脸上都困意倦倦,结束了一整晚的工作心情都十分愉悦,其中有一个帅小伙,一眼就看中了想要画他,起初他不同意急着赶回家,我们赶紧和矿工小队长商量才终于让他答应了。
把他带到了井口的小平房,让他给家里打个电话,他用满口的山西话说不记得号码了,是担心电话费还是忘带了?我掏出手机给他用,他依旧拒绝了,看来是真的不记得电话了。
怕他睡着,我们就边画边聊天,一个多小时的绘画结束后就赶紧让他回家。
刚准备开始第二幅创作,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哐”的一声,门被踹开了,一群人冲了进来。
领头的人冲我们大喊:“见到马强了没有?见到马强了没有?你们干什么呢?”
我们面面相觑,“见到马强了,刚画完,他已经走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谁让你们来的?”
“我们是和矿上说过的,他们同意我们来画画……”
我们都懵了,一听到刚画完,马强已经离开,一群人又跑了。正纳闷呢,马强到底出什么事了?其中一人走到我旁边说老师不要怕,是马强没回家,马强的女人来矿上找人了。

每次升井,矿工们会在矿井口签下自己的名字,表示已安全出来,有些为了方便就会按一个印泥手印。几个小时不回家,马强的老婆就急了,就来矿里找人。找到了队长,队长说升井了,但是那些手印压得上下不齐,一时间不确定到底上来没,这下大家伙都紧张了,赶紧去澡堂找,把水池子的水放光了也没有,饭堂的人也说没见着马强,厕所也没有。不可能啊,马强不可能工装也没卸下,矿灯也没交,自救器也带着就回家了。所以就有了刚才那一幕。

仅仅只是晚回家几小时就让家人如此着急,可见矿工和家人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作为家属也时常担惊受怕着。
7年后,再次来到这个矿区,某个晚饭后在矿区外的小村庄散步,路过一个矮房子,隐约看到有几个人在那聊天,走近了,原来就是矿区的矿工兄弟们。
“你们认识我们吗?”
“认得,认得,几年前来过。”
“你呢,你认识我们吗?”
“不认识……”,我摘下我的帽子,他立马就认出了我,“啊,我记起来了,你是当时的画家,见过你们的。”
“你们村里是不是有一个叫马强的?”
“有的,有的,哎~马强,有人找你!”
远远地,就见那道身影走了过来,“什么事什么事?”
“你还认得我们吗?”
“认得的,画家!”
“你老婆还好吗?”“好的,好的。”
“那你老婆还管你管那么紧吗?”
他笑嘻嘻地说:“女人嘛,女人嘛!”他的眼睛黑亮黑亮,傻呵呵地笑着,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在他的脸上洋溢四射。
小聊了一会,我们便继续往前溜达,走之前和马强说,你别走,一会我们还来找你。

不一会太阳就落山了,四处漆黑一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回来,恍惚间看到矮墙下还有几个人坐在那,一想到也许马强还在那我们赶紧走过去想和他再聊几句,走过去一看,发现是我们的幻影,马强已经又不见了。
村落里家家户户的灯,黄黄的,一盏盏如星火般摇曳着,我们知道,马强回家了。
见到三班组了吗
我曾经画过一组画叫《三班组升井》,讲的是我在安徽某矿场的故事。

三班组升井
那时候才开始画矿工系列,这是个竖井,垂直下去800多米深,需要依靠罐笼才能下去,趁着矿工升井的瞬间,我们抓拍着素材。边上操作罐笼的人问才上来的人:“见到三班没有?”
他们说没见到,说说笑笑就走了。
又上来一组人,又问见到三班没有,大家都说没见到。
说着说着,这些人脸上的表情就比较凝重了。
我们拍着照片。身后慢慢站了很多人,大家都不走了。我们把相机放了下来,不好意思拍,也不敢拍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们就在那等着,上来一组,操作的人就问见三班了吗?都说没见到。
按理说三班早应该升井了,但他们一直没升。
所有人都站在上面安静地等待,大家的目光都汇聚到了罐笼顶部的红灯上,红灯一闪,就把电梯放下去,等啊等,一直不见红灯闪,我们一个个死死地盯着,突然那个灯闪了,我们心里又是紧张又是高兴,不知是不是三班上来了。操作的人赶紧把电梯放下去,那个矿洞好长,终于到底了,再往上拉,卷扬机就着钢丝绳咔哧咔哧地响。电梯上来的一瞬间,一班组,6个人,整整齐齐,没错,是三班,是三班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操作罐笼的人把门打开,冲着那个人就劈头盖脸的去打,被打的那个人就笑呵呵地说,走岔了走岔了。这些人一出来,操作的人就照着领头班组长的屁股狠狠的踢了两脚,班组长依旧乐呵的回头说走岔了走岔了。周围的矿工们,都笑着拍拍三班组的矿工们,勾着肩说说笑笑的就走了。
这就是最淳朴的兄弟情吧,嬉笑怒骂下是对矿区兄弟的担忧与害怕。
这组作品我一共画了11张。名字就叫《三班组升井》。

周刚 1988年中国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1992年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研修班毕业;1998年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99年中国美术学院水彩高级研修班毕业。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水性材料绘画工作室主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水彩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艺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