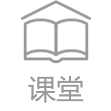近日,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童中焘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张伟平、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张雨婷就中国画笔墨问题进行了讨论。
“笔墨当随时代”还是“笔墨当随古代”?笔墨之外的第三要素是什么?“水墨画”与“中国画”的争议......现将此次论艺谈话整理成稿,集中归纳为三大问题,以飨读者。
笔墨当随何代
好笔墨与坏笔墨的判断标准
张雨婷(以下称雨):关于笔墨的讨论已有很多,最近我看到一组很有意思的说法:“笔墨当随时代”与“笔墨当随古代”,两者一古一今,似乎争锋相对,童老师您怎么看呢?
童中焘(以下称童):无论是“笔墨当随时代”,还是“笔墨当随古代”,我们都不能简单地下判定,对或错。因为“笔墨”的概念外延和内涵都十分宽广,这里的“笔墨”究竟指什么?“笔墨”中哪些是应该随“古代”的,哪些是不能随的——都值得深究,否则便会流于空泛。
雨:您能具体地展开说一下吗?
童:我在《中国画画什么》中,曾经详细罗列出古代书画论中提到“笔墨”时的具体指代,包含有用笔用墨、笔墨理法、结构技法、表现力、风格、气象气韵等多元因素,总结一下,我认为可以归为两点:一为用笔、用墨(这也是画家的惯常理解);一为笔墨“关系”或称笔墨“结构”。
先说用笔用墨。从古至今,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判断笔墨高下的标准已经是十分清晰的,古人在书论画论里也已说过很多,这是千古相通的,因此不存在“随”还是“不随”时代的问题。
雨:您说到对笔墨的判断标准,能否进一步举例说明呢?
童:黄宾虹说:“画有笔墨章法三者,实处也;气韵生动,出于三者之中,虚处也。”笔即“骨法用笔”之“用笔”。但用笔的范围太大,可能有“骨”,也可能无“骨”。黄宾虹总结出的“五笔”(平、留、圆、重、变),就是对用笔的要求。也就是判断“有笔”或“无笔”的标准。
他还同时提到,五者是“用功的方法”,就是有力和怎么用力的运笔的训练。而书法用笔与画法相通,黄宾虹的“五笔”就是用书法的点、画(如印印泥、屋漏痕、折钗股、万岁枯藤)来解释平、留、圆、重。
点画是形迹,然而形迹后还有精神,例如“平”——一画一波三折、有起伏、而处处实在,没有一处虚浮——其实说的就是诚、信。如孟子所说:“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又如“重”,比于万岁枯藤、高山坠石,如金之重而柔,铁之重而秀,扬之为华,按之沉实,重而不浊不笨顽。
以上都是做人的道理,所以黄宾虹说,作画“以德为归”,用黑格尔的话则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又如“留”,书法用“如屋漏痕”作比。就像墙壁上的水流下的痕迹,自然,不勉强、不做作。
雨:用笔有标准,用墨也有什么标准吗?
童:确实。黄宾虹以自己的实践为基,提出“七墨”的标准(七墨:浓、淡、破、泼、积、焦、宿)。后来又加入了渍墨和亮墨,可统称为“九墨”。但是,不管是“七墨”还是“九墨”,讲的都是审美要求/标准,它们有的指材料,有的指墨的运用,因此在概念上无法与“五笔”对称。我因而自己总结了用墨的五个标准:清、润、沉、和、活(详细参见童中焘《“笔墨”与“中国水墨画”》一文)。
张伟平(以下称张):其中“和”与“活”看似类似,但两者的差别要仔细区分,“和者不寡”,指对整个画面的把握和组织,而“活”则指的是画面的生命力。有些画看上去画面很稳妥,布局、笔墨处理都合理,但是不“活”,死气沉沉,是“死墨”。究其原因,是画家在作画时没有注入自己的生命能量和气息。
当然,笔墨的“活”不止是让画面墨笔的变化去表现自然界的物性变化。比如雨后山峦乍晴时呈现的云烟明灭变幻无常的状态,如果它们未能与画家的“情”相融,则它们仅是山体经雨水冲刷后的物性表现。而如果画家能在此景中有所感应,进而将此物性感受与自己的内心情趣变幻联系起来,那么它们就转化为了画家的“笔墨”信息,承载了画家的生命信息而变“活”了。
雨:那就是说,只要我们拿着笔和墨,想要画的是中国画,就脱不开刚才您说的用笔和用墨的标准了?
童:对。我想标准是不会变的。因为笔墨中蕴含的人性和人情也是不变的。当然,随着时代不同,人性和人情的外延会有扩大或缩小,但在根本上不可能大变——“继之者善也”。所以才说,古今用笔和用墨的标准是一致的。
结构的重要性
笔墨之外的第三要素
童:我们谈“笔墨”,往往都默认是指“用笔”、“用墨”,这实际上是有缺失的。这也是我认为“笔墨当随古代”这句话不妥的重要原因。回到上面我提到过的笔墨的另一个内容:点、画的关系和结构。
为了更好理解,我们可以把它和书法做一个类比。书法强调的点、划,就是画画的“用笔”,但别忘了书法还有一个重要组成,结构(结体)。这具体表现为每个单字的间架结构,以及字与字的联络、行与行的关系。这样就构成了一幅书法作品的章法。而每个人的结体是千差万别的,要怎么去“随古人”呢?
张:对。这让我想到颜真卿的《祭侄稿》。以筋骨丰厚的楷书闻名的颜真卿,声泪俱下时写下的《祭侄稿》,完全展示了其另一种艺术风格。如果我们要“随古人”,又怎么去随那种“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悲痛呢?
童:画比书法更加复杂。明代赵宦光说:“能结构,不能用笔,犹得成体。若但知用笔,不知结构,全不成形矣。”不善于用笔,还是汉字,如果只知道用笔,不知字的结构,那就不成书法了。因此可以说,用笔为材质,结构为形体;用笔为姿容,结构为形貌;用笔为善书,结构为能文;用笔为性,结构为情。画的形式,最显见正是形貌。近百年来,中国画最受诟病的,就是总是“老样子”。而所谓的“创新”,就是搞形式上的花样。
张:潘天寿不一样。
童:对。山水画上则是黄宾虹、李可染,他们两人有划时代的意义。黄宾虹说:“画看笔墨章法三者,实处也。气韵生动处于三者之中,虚处也。”古人则说:“离而合。”离在于面目,合在于精神。看画,首先观整体气象,细看笔墨、布置。
“章法”包括了布置及其相互关系。布置指安排画材以成势。画材本身的形象如一朵花、一只鸟,就有一个点画组合的关系。结合得好就活,结合得不好,就僵化。山水画是从一棵树到一丛树,从一块石头到几块石头。相互联络扩大成整体,都是点画的结构关系。所以我说点画的“关系结合”即结构与结体,也是“笔墨”的应有之义。所以讲“笔墨”,只看到用笔或用墨,是不够的、片面的。
雨: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把“结构”看做“笔墨”的一部分,是广义的“笔墨”?
童:一个概念,内涵会随着需要(社会发展的现实)而扩大,这是中国传统的普遍状况,如“气”“理”等。在西方,常会造一个新名词,而我们习惯沿用旧概念。这一做法有利也有弊。利是包容性大,弊是让不熟悉历史的人引起理解上的偏执。如果一个概念被赋予了精确的定义,其实会造成片面和局限。比如“笔墨”这一概念,在中国画史的不同历史阶段,内容就在不断充实。
雨:在传统画论中,不是也有“结构”的提法吗?
童:确实如此,但它是作为动词使用的。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画论中常说的“参差”“承乘”“断连”,或是“浓淡”“干湿”“详略”“简繁”,乃至“黑白”“虚实”,还有形的大小、高低、正侧等等,我认为讲的都是“结构”。只是那时的古人并未抽象出“结构”一词。黄宾虹讲的“不齐”与“不齐之齐”,就是讲“结构”的原则。他的许多山水,从一边生成一大块,大块里面笔墨结构的变化,造成各种不同的镜像。他本领大,因此离古人的面目也越开。画是写形的,掌握了这个写形的原则,去画出自己的感受,就不会是“复古”了。
雨:如您所说,一般人只认用笔用墨,没有认识到结构也是笔墨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童:这跟中国画的历史有关。中国画史可以看作是笔墨的发展史,简要概括,就是:线—用笔(早期画家如顾恺之、陆探微、谢赫等)—用墨(山水画兴,五代荆浩提出用“墨”,从此笔墨并用)—元人“以书入画”—明清深化(提倡笔精墨妙、发扬个性)。山水画在中国绘画史上自宋代成为主流,在表现技法上,我们称宋人为“大成”,元人是“潇散”宋法,明人“守成”,后来则是“成法”的个人运用。因为后人注重“守法”,所以就会着眼于如何“结构”以成法,而缺乏打破“成法”的“结构”观念。自然也就少了以“结构”为观念的“创法”。黄宾虹简出“不齐”与“不齐之齐”,正是说“结构”的“大法”。
张:这点很重要。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大法”,那就会有新形式和新面目了。
童:是的。各人能够表现自己的性情:写情者尚形,作品中的形象、整个艺术形象,就可以随着各人的不同情感或随着时代的转移而发生变化。因此,笔墨表现是没有止境的。
简单概括起来,就是精神可随,而形迹不可随。譬如王蒙的画,解索皴,感觉好像和早期顾恺之“高古游丝”的用笔差很多,但王蒙只是把用笔的形迹变了而已,顾恺之那有力、沉厚的笔法并没有变。每个时代、每个人会选用不同的方式表现,这是一定的。“笔墨当随古代”这类想法很明显是针对石涛提出的“笔墨当随时代”。
依我的理解,我们不应该把笔墨当随“时代”和当随“古代”对立起来,而是可以把它们看做互相补充的一个整体,即笔墨当随时代,笔墨又不随时代。“用笔千古不易”,用笔的迹象因人而异;笔墨千古不移,笔墨的形貌因人、因时而异。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离而合”,本领愈大,愈能高。
技与道争
有墨无骨的用笔叫做“墨猪”
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很多当代画家选择了“实验水墨画”这一表现方式,从他们打出的名号就不难看出,“水墨画”实际上缩减或无视了“笔”在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是认为“笔与墨争”,就可以舍弃中国画“笔墨之道”中的用笔部分呢?
童:用墨以用笔为基础,所谓骨法用笔,传统观念认为没有骨法的用墨不算真正的用墨。
张:所以当代很多画家,纯粹追求墨在纸上显示出的各种肌理和效果,甚至直接用墨往纸上泼,是误入中国画的歧途了。
童:早在唐代,张彦远就说过“不见笔踪,不谓之画”。当时王洽以泼墨著称,世称“王墨”,张彦远这话就是批评他的。因此,墨法里也要有“骨法”,有骨有干才能立得住。
张:我们当代很多人自以为科技讯息发达,比古人的眼界和智慧都高出一截,所以创造出了纯水墨效果的中国画,并兴致勃勃地沉溺其中,费了好多功夫去专研墨色、墨效,将用墨与用笔截然分离;其实只要读读画论就可见,冲、泼印墨并不是我们才会玩的“新墨技”,不能流传下来是因为这些“新技”与中国画传达高质量生命境界的核心价值理念背道而驰。
童:古人讲“筋、骨、血、肉”,所谓“骨具则筋络可联,骨立则血肉可附”。这里已经不只是技法问题了,“笔墨”是一个文化概念。之前一个问题提到的“标准”,是以人为标准。钱钟书先生曾说“评文,当作人看”,这里移以评画,有墨无骨的用笔叫做“墨猪”,软骨头的人,同样被人看不起。
“中国画”何以成立
不能以“水墨画”代“中国画”
童:接下来我还想谈谈关于“水墨画”这一概念。现在很多出版物刊登作品,多以“水墨画”冠名,其中却包括青绿和工笔画。我对之是抱着批判的态度的。
首先我们看“水墨画”的提出,是近20年从中国台湾那边热起来的。一些理论家想以“水墨画”取代“中国画”。其实他们根本没弄清楚这两个概念。从学理上分析,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中国画”何以成立?
张:这个问题有意思了,可以说直击中国画的核心问题。从事物的源头到高度,直接到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为什么学习中国画。
童:讲艺术,就要讲艺术的高度,中国和西方都有各自的艺术高峰。中国画的高峰在宋元。我们看待中西方绘画应该抱着“以异求同”的态度。异是同的基础,比如“概念”是从众多个体中抽象出来的,共性是从个性里抽象出来的,我们古人叫做“殊途同归”。
既然基础在于异,那么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画的基础性问题,要搞清楚中国画和西画不同在哪里,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中西绘画所追求和表现高度有何不同?我们再谈谈中国画的根源,邓以蛰先生早就研究过,我们早期的“绘”与“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考工记》对当时的艺术工匠所从事的工作也有记载,简单讲来,用色的乃绘,用线的为画。
古人分工明确,而“绘、画相需”。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画”是指什么。汉魏晋以来逐渐确立并成熟的中国画,书法通于画法,是以笔线表现为主体的。
当然,这里也有“绘”的部分,比如在六朝唐蓬勃兴起的佛教艺术,就是以“绘”为主的,如“没骨法”、“凹凸法”等画法,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外来的表现手法,但我们并没有被他们同化过去。
因此总体说来,中国画的传统还是建立在早在顾恺之时期就确立的“用笔”基础上的。再追根溯源,就又回到了那句“书画同源”。
张: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采用并一直发展这种以用笔用墨为主的绘画形式。虽然西方那边的东西也很好,但我们中国画的“体”已经确立,只是借鉴、汲取,不断丰富,却不会被同化。
雨:对。所以有些说法,比如“书画同源”、“骨法用笔”,虽然像是老生常谈,但我们还在反复强调,因为这是中国画的根本性概念和原则性问题,很多是非判断都建立在它们之上。很多中国画家,甚至评论家,在面对一些当代艺术现象时,常有惊人之语,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概念混乱、原则模糊,不能从事理和源头上进行分析和判断。
童:所以为什么说“水墨画”的提法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呢?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那就是吴冠中所谓的笔墨工具论。笔墨怎么能仅仅看成一个工具呢?笔墨“流美”啊!与写“形”为一体的笔墨,本身便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它本身就是一种感性的呈现。
张:而且这“美”,是与人性相合的,不仅仅指自然美。如果谁提倡把笔墨仅作为状物工具或为迎合视觉规律的变化加以改变,那就等于弱化与否定了中国画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就与中国画的“罪人”无异。
童:总结一下,“水墨画”和“中国画”有以下两个差别:
第一,中国画的范畴大于水墨画,因为中国画还包括青绿、金碧、浅绛、工笔等画法,所以不能以小代大。
第二,这是根本区别,中国画讲骨法,而在水墨画家的观念里,水墨就是工具,是不讲“骨法用笔”的。这和我们刚才讲的中国画的核心概念是背道而驰的。清人范玑说“画以笔成。用笔既误,不必论其画矣。”
王学浩又说“作画第一论笔墨”,虽然有些片面,但不无道理。道理在于“笔墨”表现是中国画的“一元”,而且是艺术高峰的“一元”。
文章来源: 美术报
原文链接: 点击查看原文